(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法国新增2320例,累计确诊5803049例,新增死亡33例,累计死亡110891例;
更多欧洲疫情数据,请浏览文末疫情图。
编者按:日前,复旦大学海归教授因“升迁”困境报复杀人一案震惊寰球,再次将“非升即走”这一当前中国学术界人才流动与上升普遍存在的“制度”暴露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学术与竞争,人才与职位,学界金字塔应如何搭建非常适合国家利益与人之常情等等问题,持续拷问东西方各国相关制度。美国、中国、欧洲孰优孰劣,对未来学术事业健康发展有何影响,值得关注。
就此,本报记者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采访当地多位教授,以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制度的比较与鉴别中,给读者以启发。
董长治教授谈法国大学的教师聘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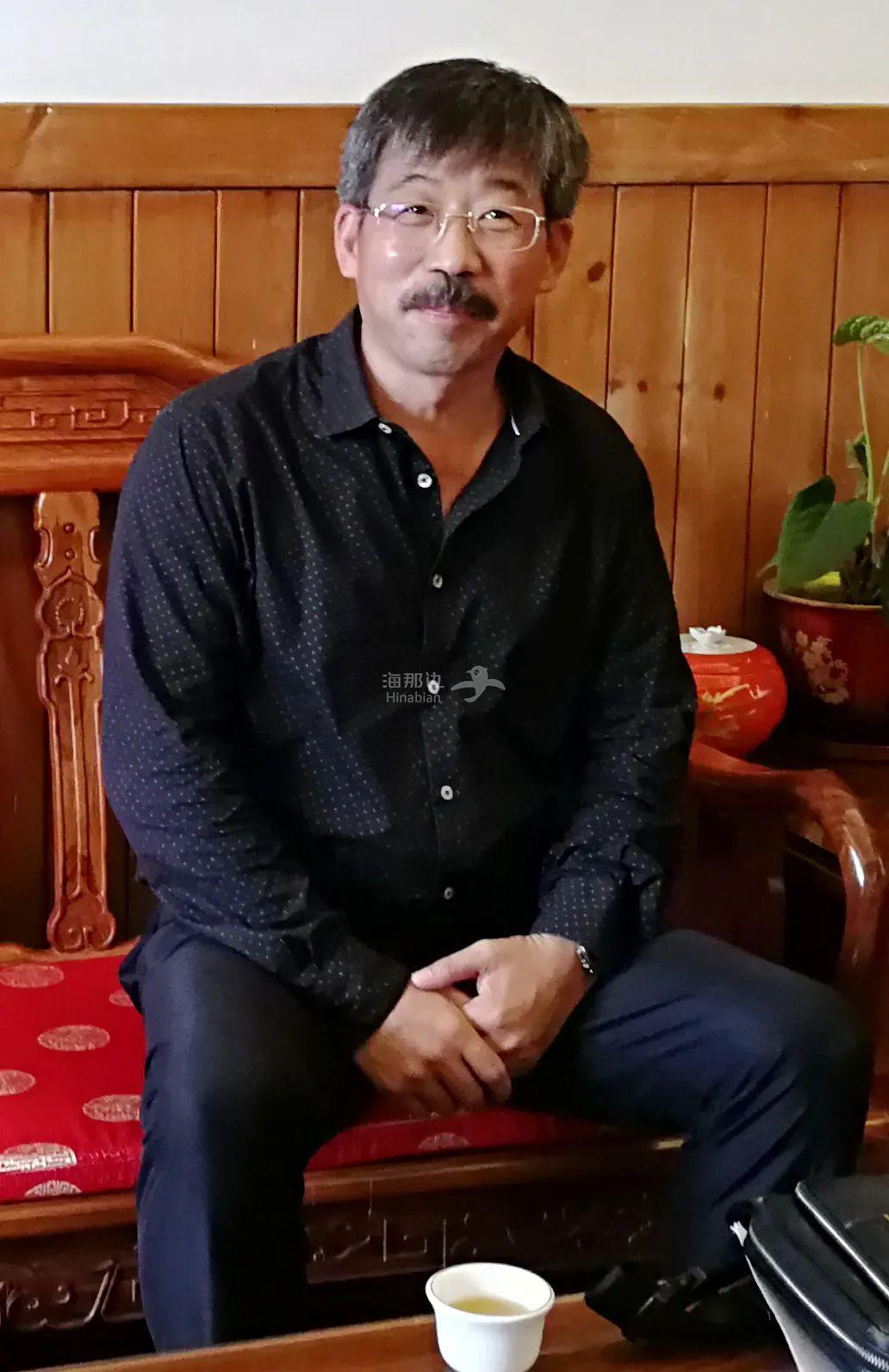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董长治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法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2009年加盟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建的ITODYS 实验室,并于 2011 年晋升为教授。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学术界“内卷化”严重是全球性问题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曾敬涵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和宗教系教授。作为海外学者,曾敬涵对复旦大学此次事件非常关心,他表示此事件在学术界是件大事,牵扯到学术界晋升机制和未来发展,以及中外学术界的对比。
中国目前引用美国“非升即走”制度,曾敬涵认为,这套制度体系相对来讲还是公平的,它给了所有人相同的机会,如果科研水平及相关水平达到条件便可留下来,如果不够,那就可能面临离开。这是美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来大学发展留下的产物,也是美国教授晋升体系最主要的一个指标。他坦言,将这套体系引入中国后,实际情况不同,会存在一些中国特色,例如参与评比人数远大过可以留下的名额等等,让竞争变得过于激烈“内卷”,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
悲剧的发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个人原因、“非升即走”的制度乃至于社会大环境下对于维权制度的认知都是酿成这场悲剧的因素。曾敬涵强调,“非升即走”制度只是该事件中的一环,不应把过多目光聚焦于此,只怪罪这个制度。
英国学术界的升迁制度和美国相比不同,曾敬涵介绍道,英国大部分讲师入职后会直接签订终身合同,也就是终身教职(Tenure)。虽然讲师有一至三年的试用期,但这个试用期并不是一个评价体系,而是工作体系,也不涉及到非常严谨的学术评价等。
相比下,美国的制度会在讲师入职几年后将其成果送到学校外进行相对严谨的外审。英国的制度对于对于刚入职的学者来说更像是所谓的“铁饭碗”,给了学者一切保障后学者开始进行科研。相比之下,两种制度各有利弊,英国制度保障性强,但容易抵消学者的科研动力,而美国制度虽能够时刻鞭策学者,但长远来讲可持续性较低。
学术界出现这样的悲剧,其实体现出很多根源性问题。目前学术界越发内卷化并不是只有中国才出现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现象。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近几年的高校扩张,导致了博士数量激增,但教学岗位却不会因为的博士数量上涨而随之上涨,因此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同时也造成博士学位贬值。英美目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 内卷,本意是一类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的形态,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现象。现指同行间竞相付出更多努力以争夺有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现象。可以看作是努力的“通货膨胀”。
其次,在内卷化的情况下,获得教职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高。近期美国研究发现,以前学者拥有好的学位就有可能获得助理教授职位,而现如今至少要发表两篇文章才能够拿到该职位。几年后发表文章篇数要求还可能会增加。曾敬涵拿他曾任职过的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举例道,他申请时一个国际关系讲师的职位有 200 个人申请,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是不会有这么多人同时申请一个职位的。
谈到人才归国对于中国制度的不适应,曾敬涵坦言,不管在哪里,只要生活和工作环境遭到改变,一开始都会有些许不适应。一般来讲,三年是过渡期,在三年内人们一般会逐渐适应当下的生活、学习、工作环境,这是普遍现象。他提到,中国引入海外人才是希望海归能够使中国教育制度更加国际化,因此怎样能够更好照顾到海外人才,为他们提供良好科研环境,曾敬涵认为是现如今需要思考的问题。
德国大学教授用人制度:聘任体系,而非升迁体系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丁永健
德国马格德堡-斯滕达尔应用科学大学工业自动化教授、主管教学和国际合作的副校长、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副会长。
和国内一样,在德国大学获得教授职位并不容易。“招聘时根据专业,几十个人里挑一个是常见的事”。
现任德国马格德堡 - 斯滕达尔应用科学大学工业自动化教授、主管教学和国际合作的副校长、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副会长丁永健教授介绍称,根据德国高校校长联合会的数据,德国总共有 390 所高校,其中综合性大学(Uni)120 所,应用型大学(HAW)213 所,艺术和音乐学院57所。德国以公立高校为主(240 所)、私立为辅(150 所,包括教会学校和纯私立学校)。德国公立大学的教授一般为终身公务员制,分为 W1(青年教授),W2(类比国内普通教授职位),W3(类比国内教研室主任职位,包括讲席教授)三类。
和国内一样,在德国大学获得教授职位并不容易。“招聘时根据专业,几十个人里挑一个是常见的事”,丁永健教授介绍说:“2020年德国总共约有48500 名在职教授,其中大约25% 为女性,比例在逐年升高。德国公立大学包括公立应用型大学教授以终身公务员性质为主,国家根据学校大小和学科配置,规定教授名额,所以通常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教授退休、跳槽或新增学科教席时才会公开招标。”
德国的应用型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一样,也是培养学士和硕士为主。少数应用型大学比如萨安州今年开始拥有独立博士授予权。核心区别在于综合性大学偏重于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教学上偏重理论。应用型大学设立的教授岗位以 W2 级教授为主,极少数学术带头人或者领导岗位会招聘正 W3 级教授,基本上不设立青年教授(W1)职位。“最常见的升迁途径就是跳槽,从一个学校的 W2 教授职位跳槽到另一个学校的W3教授职位”丁永健教授说。
“曲线”应聘教授职位
应用型大学在招聘教授时的标准与综合性大学有所不同,“应用型大学重视教授们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包括教学能力,对论文要求次之。比如工科教授一般要求有 3 年以上工业界经验。如果候选人在某公司有成功研发经历,在招聘委员会眼中往往比纯粹论文更加重要。”因此,拥有 17年工业界从业经验的丁永健教授建议年轻华人学者和专家到工业界一线工作。“有志于到应用型高校任教的年轻华人专家,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不建议再走博士后道路,而是应该去工业界、经济界的一线工作几年。如果在企业干得顺利,成为了团队经理或研发部门主任,那么未来可以尝试申请应用型大学教授职位,如果在工业界期间有高质量学术论文发表,那可以去试试应聘综合性大学正教授职位。”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曲文敏
德国萨尔州应用科学大学工程学院教授。曲文敏教授建议华人学者积极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善用德国各类型大学提供的机会。
“青年教授职位可以帮助年轻学者开展自己的独立研究,而且青年教授 6 年合同到期后,在许多正在扩充学科教授队伍的大学,通过考核并升迁的成功比例很高”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蒋晓毅
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系主任。
“青年教授是德国近些年新引入的概念和职位,意在为年轻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更稳定的岗位,加强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和计划性。”
升迁途径多元化 华人学者影响力增加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曾安平
汉堡工业大学教授、生物工程和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德国国家工程院 (acatech) 院士、德国华人教授学会会长。
汉堡工业大学教授、生物工程和生物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德国国家工程院 (acatech) 院士、德国华人教授学会会长曾安平教授介绍了研究型工科大学的教授招聘情况。曾安平教授称,除个别学校外,有 tenure track 的青年教授职位还相对较少。但德国联邦教研部鼓励大力增加 tenure track 的青年教授职位,许多学校也在为此做出努力,进行多元化改革。“如汉堡工业大学通过和工业界的合作,共同设立由企业资助的青年教授职位,这些教职一般没有 tenure track 合同,但获得者几年后竞争 W2/W3 教职机会很大”,曾安平教授还补充说,青年教授在获得其它高校 W2 或 W3 职位后,优秀者在本校也有可能通过和校方谈判升迁为 W2 或 W3 教授。
德国大学在录用教授时非常重视“保证教授质量,并和学科发展方向契合”。因此,曾安平教授建议希望应聘教授职位的华人年轻学者“研究要做好,研究能力要过硬”。想要实现更高的目标,就要“沉得住气,心无旁骛地做研究,不要急功近利”。同时,“提高在研究团队里的参与度,在确保自己专业能力过硬的前提下,提高组织管理和独立申请研究基金的能力。”
蒋晓毅教授认为,德国大学对于教授升迁的考核标准主要是“科研和教学成就、学术界活跃程度和申请科研项目的能力”。他建议年轻的华人学者和研究人员脚踏实地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锻炼“展示自己实力的能力,希望年轻学者充满自信地展示自己的实力”。
曾安平教授还介绍说,近年来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发展迅速,尤其是 W1年轻教授和女教授增加比例较大,有的甚至是直接从国内应聘而来。教授学会已从成立之初的十几人发展到超过 70 多人。“越来越多的华人教授开始担任重要职位,如讲席教授,研究所所长和系 / 校领导等,相信年轻的华人学者会在德国大学和学术界有更大的发展和能见度,做出更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