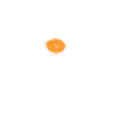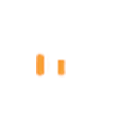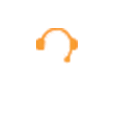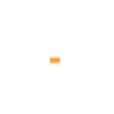本文来源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朱苏力。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
[导读]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盛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寰球首要。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
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
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
▍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
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
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
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
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
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知名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
若是关注知名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确实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
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
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
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知名研究生的较高水平超过20年前知名研究生的较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
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
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
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知名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知名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知名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知名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知名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
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
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
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
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