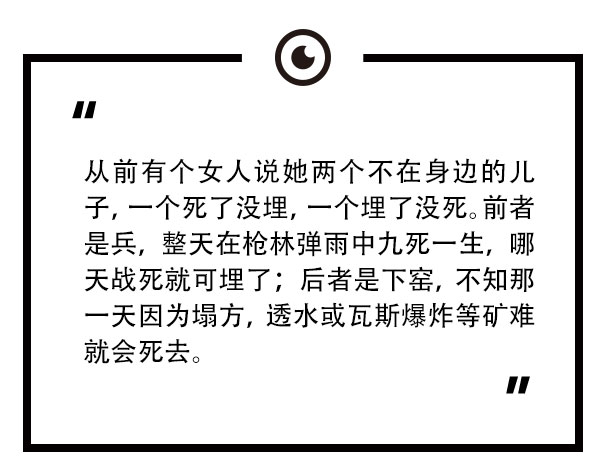(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这是 Hinabian 的第 1 个
新 移 民 故 事 ▼
军人张振华
1934年,张振华出生于合肥的一个小县城,因财产纠纷,父亲被三伯雇凶杀害。少年孤儿的张振华被四伯母收养,此后他的人生,可谓是命途多舛。
四伯母是湖广总督段芝贵亲侄女,为把张振华教育成才,着实费了不少功夫。然而,初入学堂的张振华对什么“学而优则仕”、“知识改变命运”这类念头,都是没有的,不过是随波逐流,一直到1949年。
忽然有一日,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在国民党撤退半日后来到了张振华所在的城市。少年张振华好奇地跟着他们,从府学到县府门前,他们身着粗布衣服,步鞋步袜,态度和蔼说话客气深深的吸引了他,经过多次缠磨,少年张振华终于如愿的参了军,那时他还是一个不满14岁的初中2年级的学生。
此后,张振华历经文工团员、宣传干事,文化教员,从合肥行军,经皖南,越北到杭州又到温州。1954年,张振华结束了6年的军营生活,从嘉善转业到北京,进入宣传部门。进单位后,张振华面对的不是25和38的老干部就是全国盛名高校的毕业生,像他这样万金油似的既无资又无才能的人,有些自惭形愧。于是,张振华决定继续读书。
1955年,在没有复习资料又无人辅导的情况下,张振华考上了山西师范学院历史系,老师的器重和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稿,令他文思泉涌,也有些飘飘然,谁知福兮祸之所伏,不过两年,张振华就因为对国内外形势发表了些看法,被迫离开了学校,送到太原市郊高家堡农场劳教三年。
祸兮福之所倚
那个时候的张振华感到命运弄人,可少年人,哪里分得清什么是福祸相依呢?
1958年大战钢铁,张振华住在太原西铭一家车马大店,负责验收焦碳。一个老人同他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个女人说她两个不在身边的儿子,一个死了没埋,一个埋了没死。前者是兵,整天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生命已在阎王爷的帐簿上勾去了,哪天战死就可埋了;后者是下窑,整天埋在六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底层,不知那一日之内因为塌方,透水或瓦斯爆炸等矿难就会死去。
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偏偏士兵和矿工这两个在社会上被人鄙弃而又危险的职业,张振华都干过。在军队呆了6年后,张振华当了18年矿工。
特赦战犯后,才放出了右派。重新做人的张振华选择了挣钱多的下煤窑的工作,虽说当矿工危险,但工资一个月100多块,至少解决了生计问题。一般矿工的工资有两大开销,一盖房子二娶妻,即使下井十几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张振华也只吃几分钱的浇汤面凑合着,至于娶妻,张振华却是不敢想的,一个棋局中被随意拨拉摆布的小卒,只能四处漂泊,自身泥菩萨过河,哪敢再娶妻育子贻害后代?
那段当矿工的岁月,常常在张振华的脑海中涌现盘旋,幸运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振华做了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幸亏当了工人,否则运动来了,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以张振华的个性,怕是……
我为什么辞去教师?
很快运动来了。对全国是莫大伤害,但对矿工来说,不用下坑也能挣钱——从四矿下坑,转一遭从另一个口出坑到一矿,再乘矿交车返回澡堂洗澡,一个班就完了。
好景不长,1979年,组织部找张振华谈话,派他到四矿中学当老师。当时,张振华一个月当十几天班,批十几天病假,不差钱,日子过得犹如神仙,何苦去天天教书呢?结果掘进队惹不起组织部,张振华只得去中学报导,教历史和地理。
张振华虽然没有正式教过书,但胜在读书多、口才好。梁启超说“兴趣是较大的原动力”,这句话也是张振华的教育理念,张振华认为,只要把丰富多采的历史讲得津津有味,吸引住学生喜欢,至于其中人名地名和年代了,他们慢慢地就会自然记住的。
文化知识在长期荒芜的年代里,孩子们就像跋涉者困居在沙漠中,能送一些水去滋润他们干涸的心灵,当然是欢呼雀跃。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头一年学校设了补习班,每节课8毛钱补足。语文、数学、政治是上大课,物理化学与历史地理分开上。教导处有位年事已高的史老师,每月发放补习班代课费,见到张振华总要以一种异样目光打量他,因为张振华出力少而拿钱多,理科50多人,文科才4人。直到高考成绩公布后,他才另眼相待。
因为理科推了光头,50多人连个技校生也没有,而张振华带的文科班,4人全部命中——一个大学,两个中专、一个技校,考上大学的人,数学分数与钱钟书先生考清华的分数差不多,全是史地拿了高分。为表示歉意,那位史老师挥毫给张振华写了个刘禹锡诗句的条幅:“千淘万沥惟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张振华至今仍珍藏着。
张振华当教师已经是人到中年,也算是从业中的佼佼者,他却突然决定不干了。
其实,他本人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教书对他来说既是爱好又是份内工作,讲课驾轻就熟之余,每年还有寒暑假自由支配,除此之外,在学生面前还备受尊敬,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张振华又要毅然的放弃这神圣的职业?
原来,张振华对中国古往今来所保持的教育制度——所谓金榜题名的实用教学法非常不满意:校长、班主任和所有教师,首先考虑的总是今年有几个人可以考上大学,几个尖子生就是宝贝蛋,如何保证尖子生的进步才是重中之重。其他人都是陪读,只要不捣乱,他们学不学习无所谓。
令张振华吃惊的是,那些当年为他们付出心血较大、下功夫最多的学生,如今功成名就了,见到昔日之师却未必笑脸相迎,往往视如路人;相反,那些未视作重点培养对象的孩子,见到老师却异常的亲切与尊敬,甚至还会觉得自己对不住老师,没有好好聆听教诲,学习成才。
这样鲜明的对比,让张振华无地自容,悔不当初。
当年若是偷渡一走了之,
会是怎样的光景?
受了一辈子罪,按孟子所说的,怕是差不多全做到了,苦过心志,劳过筋骨,饿过体肤,穷愁撩倒,做事不顺。然而,老天自始至终也从未降过什么“大”任给张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