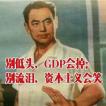- 海那边服务热线电话:
-
深圳: 0755-86938380(客户服务)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819号深铁金融科技大厦19A层
-
北京: 010-85951808(客户服务)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SOHO 2期C座 C3-3
-
上海: 020-85951808(客户服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01号国华人寿大厦301室
-
杭州: 0571-88016401(客户服务)地址: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18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D区1005室
-
如果想那就去做吧,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写在前面的话:因为熹文生活在新西兰,所以经常会收到朋友们咨询出国的问题。有还在读书的朋友说很想在毕业后来新西兰体验间隔年;有已经上班的朋友想靠自己的能力出国进修;也有一些人生触礁的朋友希望换一个新的环境生活……如果你现在不满三十岁,我一定要推荐给你我出国的方式,只需要800元申请费的新西兰打工度假(Working Holiday)签证,让你可以拥有长达1年的时间在新西兰体验异国生活。在这1年的时间里,你可以靠工作(很多种类)赚取生活和旅行的费用,并且在这期间内决定自己的去留:如果不喜欢新西兰,可以随时离开;如果喜欢这里,也可以申请其他签证留下来,并选择读书或工作以及更多的出路。在我收到的关于出国咨询的问题中,最常见的是,“我家境普通,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国了?”熹文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对于想靠自己的能力出国的朋友,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是我所认为较便宜,也是最理智的出国跳板。下面就是关于新西兰打工度假签证从申请到选择去留的纯干货分享。打工度假签简介从2008年开始,新西兰政府每年会向1000个满足一定条件的中国公民签发打工度假签证,即working holiday visa。成功申请到
-
加油!加油!因为爸妈只有你文/杨熹文我人生中只此一次觉得不该坚持梦想的时刻,是出国后的第三年,我首要次回家小住二十天,因为有事要去朋友的城市,才在家停留了几天便没心没肺地拿着行李上路了。那天早晨我送妈到公司班车车站,再转身去找自己的公交站,过到马路对面的时候,下意识地转头看,车水马龙的热闹清早,街边挤满卖早点的摊铺,越过小贩激烈的叫卖声,我看见那站在马路另一头的我妈妈,整个人呆呆地望着我的方向。这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肩膀耸动,鼻尖通红,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流满了整张脸,她看着即将离开自己的女儿,*伤心地哭成了孩子。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雨,在赶往朋友城市的一路上,窗外的景色都是湿答答的暗色调。我在心里狠狠地扇自己耳光,甚至几次下了决心,不然就不走了,永远和爸妈在一起。这是我离开家三年后首要次回家,作为爸妈只此的孩子,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可我总是能为这件事找出若干冠冕堂皇的借口,“学校假期好短啊,我有很多功课要做的!”“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很好,不想因为回国就辞掉!”“回国几周这边的房租还要照交,多不划算啊!”……二十几岁的我,实在是个没良心的年轻人,我认定自己是个闯四方的女汉子,而不是我妈想让我成为的乖乖女
-
谢谢朋友因为爸妈只有你文/杨熹文我人生中只此一次觉得不该坚持梦想的时刻,是出国后的第三年,我首要次回家小住二十天,因为有事要去朋友的城市,才在家停留了几天便没心没肺地拿着行李上路了。那天早晨我送妈到公司班车车站,再转身去找自己的公交站,过到马路对面的时候,下意识地转头看,车水马龙的热闹清早,街边挤满卖早点的摊铺,越过小贩激烈的叫卖声,我看见那站在马路另一头的我妈妈,整个人呆呆地望着我的方向。这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肩膀耸动,鼻尖通红,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流满了整张脸,她看着即将离开自己的女儿,*伤心地哭成了孩子。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雨,在赶往朋友城市的一路上,窗外的景色都是湿答答的暗色调。我在心里狠狠地扇自己耳光,甚至几次下了决心,不然就不走了,永远和爸妈在一起。这是我离开家三年后首要次回家,作为爸妈只此的孩子,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可我总是能为这件事找出若干冠冕堂皇的借口,“学校假期好短啊,我有很多功课要做的!”“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很好,不想因为回国就辞掉!”“回国几周这边的房租还要照交,多不划算啊!”……二十几岁的我,实在是个没良心的年轻人,我认定自己是个闯四方的女汉子,而不是我妈想让我成为的乖乖女
-
写作从来都是由内及外的表达因为爸妈只有你文/杨熹文我人生中只此一次觉得不该坚持梦想的时刻,是出国后的第三年,我首要次回家小住二十天,因为有事要去朋友的城市,才在家停留了几天便没心没肺地拿着行李上路了。那天早晨我送妈到公司班车车站,再转身去找自己的公交站,过到马路对面的时候,下意识地转头看,车水马龙的热闹清早,街边挤满卖早点的摊铺,越过小贩激烈的叫卖声,我看见那站在马路另一头的我妈妈,整个人呆呆地望着我的方向。这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肩膀耸动,鼻尖通红,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流满了整张脸,她看着即将离开自己的女儿,*伤心地哭成了孩子。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雨,在赶往朋友城市的一路上,窗外的景色都是湿答答的暗色调。我在心里狠狠地扇自己耳光,甚至几次下了决心,不然就不走了,永远和爸妈在一起。这是我离开家三年后首要次回家,作为爸妈只此的孩子,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可我总是能为这件事找出若干冠冕堂皇的借口,“学校假期好短啊,我有很多功课要做的!”“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很好,不想因为回国就辞掉!”“回国几周这边的房租还要照交,多不划算啊!”……二十几岁的我,实在是个没良心的年轻人,我认定自己是个闯四方的女汉子,而不是我妈想让我成为的乖乖女
-
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辜负青春因为爸妈只有你文/杨熹文我人生中只此一次觉得不该坚持梦想的时刻,是出国后的第三年,我首要次回家小住二十天,因为有事要去朋友的城市,才在家停留了几天便没心没肺地拿着行李上路了。那天早晨我送妈到公司班车车站,再转身去找自己的公交站,过到马路对面的时候,下意识地转头看,车水马龙的热闹清早,街边挤满卖早点的摊铺,越过小贩激烈的叫卖声,我看见那站在马路另一头的我妈妈,整个人呆呆地望着我的方向。这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肩膀耸动,鼻尖通红,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流满了整张脸,她看着即将离开自己的女儿,*伤心地哭成了孩子。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雨,在赶往朋友城市的一路上,窗外的景色都是湿答答的暗色调。我在心里狠狠地扇自己耳光,甚至几次下了决心,不然就不走了,永远和爸妈在一起。这是我离开家三年后首要次回家,作为爸妈只此的孩子,这是多么自私的行为,可我总是能为这件事找出若干冠冕堂皇的借口,“学校假期好短啊,我有很多功课要做的!”“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很好,不想因为回国就辞掉!”“回国几周这边的房租还要照交,多不划算啊!”……二十几岁的我,实在是个没良心的年轻人,我认定自己是个闯四方的女汉子,而不是我妈想让我成为的乖乖女
-
谢谢!熹文的话:下面是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出国的文章,希望给想出国或者正在海外漂的朋友带去一些正能量。曾经一同上学的朋友小A在国内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小白领,年底刚刚升了职。几年熬红眼的加班,让她告别了那个背着米奇包每天清晨挤在公交车里的青涩小女孩时代。如今的她,提着精致的名牌小包,踩着八公分的高跟鞋,开着还不算太过气的小车,再也不用在清晨拥挤的公交车上狼吞虎咽下两个肉包子,也不用在买一件八百块的大衣时咧嘴心疼了。可是她并不开心,自嘲是一只向往自由的鸟,可惜被银行卡和格子间捆住了脚。她在网上无比幽怨地和我讲:“亲爱的,我特别想去外面的寰球看一看… …”朋友心心念念的外面寰球,就在我偶尔上传到朋友圈里的风景照里面。海天相接的清澈蔚蓝,比基尼少女成群躺下的沙滩,一年四季常绿的草地上,肥硕的海鸥和人争薯条,小孩子赤着脚欢快地乱跑,牧羊犬也跟着撒欢疯掉。这样的景致,在南半球这个气候温润的城市,是最寻常的标志。朋友说,“你看,你那里没有PM2.5,没有失业的危机,没有钩心斗角的压力,只有阳光沙滩大草地。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该有多好!”而此时,我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在脸书上感慨着写下“留学近八年
-
谢谢朋友的支持熹文的话:下面是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出国的文章,希望给想出国或者正在海外漂的朋友带去一些正能量。曾经一同上学的朋友小A在国内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小白领,年底刚刚升了职。几年熬红眼的加班,让她告别了那个背着米奇包每天清晨挤在公交车里的青涩小女孩时代。如今的她,提着精致的名牌小包,踩着八公分的高跟鞋,开着还不算太过气的小车,再也不用在清晨拥挤的公交车上狼吞虎咽下两个肉包子,也不用在买一件八百块的大衣时咧嘴心疼了。可是她并不开心,自嘲是一只向往自由的鸟,可惜被银行卡和格子间捆住了脚。她在网上无比幽怨地和我讲:“亲爱的,我特别想去外面的寰球看一看… …”朋友心心念念的外面寰球,就在我偶尔上传到朋友圈里的风景照里面。海天相接的清澈蔚蓝,比基尼少女成群躺下的沙滩,一年四季常绿的草地上,肥硕的海鸥和人争薯条,小孩子赤着脚欢快地乱跑,牧羊犬也跟着撒欢疯掉。这样的景致,在南半球这个气候温润的城市,是最寻常的标志。朋友说,“你看,你那里没有PM2.5,没有失业的危机,没有钩心斗角的压力,只有阳光沙滩大草地。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该有多好!”而此时,我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在脸书上感慨着写下“留学近八年
-
ヾ(^▽^*)))熹文的话:下面是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出国的文章,希望给想出国或者正在海外漂的朋友带去一些正能量。曾经一同上学的朋友小A在国内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小白领,年底刚刚升了职。几年熬红眼的加班,让她告别了那个背着米奇包每天清晨挤在公交车里的青涩小女孩时代。如今的她,提着精致的名牌小包,踩着八公分的高跟鞋,开着还不算太过气的小车,再也不用在清晨拥挤的公交车上狼吞虎咽下两个肉包子,也不用在买一件八百块的大衣时咧嘴心疼了。可是她并不开心,自嘲是一只向往自由的鸟,可惜被银行卡和格子间捆住了脚。她在网上无比幽怨地和我讲:“亲爱的,我特别想去外面的寰球看一看… …”朋友心心念念的外面寰球,就在我偶尔上传到朋友圈里的风景照里面。海天相接的清澈蔚蓝,比基尼少女成群躺下的沙滩,一年四季常绿的草地上,肥硕的海鸥和人争薯条,小孩子赤着脚欢快地乱跑,牧羊犬也跟着撒欢疯掉。这样的景致,在南半球这个气候温润的城市,是最寻常的标志。朋友说,“你看,你那里没有PM2.5,没有失业的危机,没有钩心斗角的压力,只有阳光沙滩大草地。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该有多好!”而此时,我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在脸书上感慨着写下“留学近八年
-
总要学会一个人熹文的话:下面是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出国的文章,希望给想出国或者正在海外漂的朋友带去一些正能量。曾经一同上学的朋友小A在国内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小白领,年底刚刚升了职。几年熬红眼的加班,让她告别了那个背着米奇包每天清晨挤在公交车里的青涩小女孩时代。如今的她,提着精致的名牌小包,踩着八公分的高跟鞋,开着还不算太过气的小车,再也不用在清晨拥挤的公交车上狼吞虎咽下两个肉包子,也不用在买一件八百块的大衣时咧嘴心疼了。可是她并不开心,自嘲是一只向往自由的鸟,可惜被银行卡和格子间捆住了脚。她在网上无比幽怨地和我讲:“亲爱的,我特别想去外面的寰球看一看… …”朋友心心念念的外面寰球,就在我偶尔上传到朋友圈里的风景照里面。海天相接的清澈蔚蓝,比基尼少女成群躺下的沙滩,一年四季常绿的草地上,肥硕的海鸥和人争薯条,小孩子赤着脚欢快地乱跑,牧羊犬也跟着撒欢疯掉。这样的景致,在南半球这个气候温润的城市,是最寻常的标志。朋友说,“你看,你那里没有PM2.5,没有失业的危机,没有钩心斗角的压力,只有阳光沙滩大草地。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该有多好!”而此时,我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在脸书上感慨着写下“留学近八年
-
孤独是门艺术熹文的话:下面是我写过的一篇关于出国的文章,希望给想出国或者正在海外漂的朋友带去一些正能量。曾经一同上学的朋友小A在国内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小白领,年底刚刚升了职。几年熬红眼的加班,让她告别了那个背着米奇包每天清晨挤在公交车里的青涩小女孩时代。如今的她,提着精致的名牌小包,踩着八公分的高跟鞋,开着还不算太过气的小车,再也不用在清晨拥挤的公交车上狼吞虎咽下两个肉包子,也不用在买一件八百块的大衣时咧嘴心疼了。可是她并不开心,自嘲是一只向往自由的鸟,可惜被银行卡和格子间捆住了脚。她在网上无比幽怨地和我讲:“亲爱的,我特别想去外面的寰球看一看… …”朋友心心念念的外面寰球,就在我偶尔上传到朋友圈里的风景照里面。海天相接的清澈蔚蓝,比基尼少女成群躺下的沙滩,一年四季常绿的草地上,肥硕的海鸥和人争薯条,小孩子赤着脚欢快地乱跑,牧羊犬也跟着撒欢疯掉。这样的景致,在南半球这个气候温润的城市,是最寻常的标志。朋友说,“你看,你那里没有PM2.5,没有失业的危机,没有钩心斗角的压力,只有阳光沙滩大草地。如果我能在那里生活,该有多好!”而此时,我身边的另一位朋友在脸书上感慨着写下“留学近八年
-
是的聊天片刻今天陶朗加下雨,我的心情却很棒,早上和朋友Glenn见面,陪他练习中文对话,然后一直聊天到下午一点半。我在图书馆里坐足了三个小时,做完了待办事项的绝大部分,想起朋友对我开的玩笑,“天哪,每天写写写,如果把你的大脑打开,那里面肯定肌肉丛生!”也许是吧。窗外依旧飘着雨,这几天可以看到超级月亮,听说新西兰的地震和它有关,为受难中的人祈福。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依旧在这里,絮絮叨叨和你讲我生活中的那些事。双十一结束了,希望你的银行卡永远有为自己买一本书的余额。我和小千说,“等咱店里推荐到首要万本书的时候,就开个咱们自己的书店吧!”为这个梦想,努力。有一个姑娘给我留言,言语间充满绝望,“当我看着同龄的姑娘嫁给有钱人家,过上了我靠自己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过得上的生活,没有谋生存的压力,只有逛街spa做美容,去哪里都车接车送,回家保姆伺候……我问自己,读这么多的书,考那么多的证,在社会上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这些还有什么用?”我答应一定要写篇文章给她,这不是一个人的绝望,是一个群体的心声。随便在哪个拥挤不堪的公交车站望去,你总会望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姑娘,她们穿着高跟鞋和西装裙,极力
-
坚持自己的信念,就不会变成自己讨厌的模样聊天片刻今天陶朗加下雨,我的心情却很棒,早上和朋友Glenn见面,陪他练习中文对话,然后一直聊天到下午一点半。我在图书馆里坐足了三个小时,做完了待办事项的绝大部分,想起朋友对我开的玩笑,“天哪,每天写写写,如果把你的大脑打开,那里面肯定肌肉丛生!”也许是吧。窗外依旧飘着雨,这几天可以看到超级月亮,听说新西兰的地震和它有关,为受难中的人祈福。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依旧在这里,絮絮叨叨和你讲我生活中的那些事。双十一结束了,希望你的银行卡永远有为自己买一本书的余额。我和小千说,“等咱店里推荐到首要万本书的时候,就开个咱们自己的书店吧!”为这个梦想,努力。有一个姑娘给我留言,言语间充满绝望,“当我看着同龄的姑娘嫁给有钱人家,过上了我靠自己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过得上的生活,没有谋生存的压力,只有逛街spa做美容,去哪里都车接车送,回家保姆伺候……我问自己,读这么多的书,考那么多的证,在社会上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这些还有什么用?”我答应一定要写篇文章给她,这不是一个人的绝望,是一个群体的心声。随便在哪个拥挤不堪的公交车站望去,你总会望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姑娘,她们穿着高跟鞋和西装裙,极力
-
谢谢支持,也看过您的文章,加油写在前面的话:很多人知道我是个写励志故事的姑娘,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已经在房车上住下八个多月。在新西兰这个国家,能够以这种方式生活,乃我人生首要大幸事。我在夏天驾车走走停停,冬天则把车停在房东家的院子里,努力工作为了下一个夏天赚旅费,日子充满惊喜与期待。下面是买房车最初写下的一篇文章,文末加上了新的照片和视频,希望你喜欢,也希望有一日之内,我能在这里请你喝一杯咖啡,坐在海边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与梦想。一个住在房车上的姑娘文/杨熹文 我向我的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的微信还是炸开了。 “你疯了吗?”“为什么不去买个房子呢?”“该不会……是最近手头紧吧?需不需要我帮忙?” 别紧张,我没有失恋没有破产没有流离失所,只不过我这个89年的老姑娘,扛着所有身家,搬进了一辆89年的老房车,铺了床,生了火,在冰箱里放上一排鱼罐头和冰啤酒,真正开始了我晃荡十足的后青春生活。我的房车七米长,是那种很久前在日本被淘汰掉的20人座小巴士,飘扬过海到了新西兰,曾经被不同的人开去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事,易主几次,饱经沧桑,收关停在了一对八十几岁老夫妇的门前。这对八十几岁的前车主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这部
-
谢谢写在前面的话:很多人知道我是个写励志故事的姑娘,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已经在房车上住下八个多月。在新西兰这个国家,能够以这种方式生活,乃我人生首要大幸事。我在夏天驾车走走停停,冬天则把车停在房东家的院子里,努力工作为了下一个夏天赚旅费,日子充满惊喜与期待。下面是买房车最初写下的一篇文章,文末加上了新的照片和视频,希望你喜欢,也希望有一日之内,我能在这里请你喝一杯咖啡,坐在海边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与梦想。一个住在房车上的姑娘文/杨熹文 我向我的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的微信还是炸开了。 “你疯了吗?”“为什么不去买个房子呢?”“该不会……是最近手头紧吧?需不需要我帮忙?” 别紧张,我没有失恋没有破产没有流离失所,只不过我这个89年的老姑娘,扛着所有身家,搬进了一辆89年的老房车,铺了床,生了火,在冰箱里放上一排鱼罐头和冰啤酒,真正开始了我晃荡十足的后青春生活。我的房车七米长,是那种很久前在日本被淘汰掉的20人座小巴士,飘扬过海到了新西兰,曾经被不同的人开去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事,易主几次,饱经沧桑,收关停在了一对八十几岁老夫妇的门前。这对八十几岁的前车主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这部
-
谢谢你的肯定,亲爱的写在前面的话:很多人知道我是个写励志故事的姑娘,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已经在房车上住下八个多月。在新西兰这个国家,能够以这种方式生活,乃我人生首要大幸事。我在夏天驾车走走停停,冬天则把车停在房东家的院子里,努力工作为了下一个夏天赚旅费,日子充满惊喜与期待。下面是买房车最初写下的一篇文章,文末加上了新的照片和视频,希望你喜欢,也希望有一日之内,我能在这里请你喝一杯咖啡,坐在海边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与梦想。一个住在房车上的姑娘文/杨熹文 我向我的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的微信还是炸开了。 “你疯了吗?”“为什么不去买个房子呢?”“该不会……是最近手头紧吧?需不需要我帮忙?” 别紧张,我没有失恋没有破产没有流离失所,只不过我这个89年的老姑娘,扛着所有身家,搬进了一辆89年的老房车,铺了床,生了火,在冰箱里放上一排鱼罐头和冰啤酒,真正开始了我晃荡十足的后青春生活。我的房车七米长,是那种很久前在日本被淘汰掉的20人座小巴士,飘扬过海到了新西兰,曾经被不同的人开去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事,易主几次,饱经沧桑,收关停在了一对八十几岁老夫妇的门前。这对八十几岁的前车主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这部
-
叫人过来自己被坑。。在美国,无证移民如果是犯罪行为受害人,可以通过检举加害人并配合调查,而获得U签证留在美国,3年后可转为绿卡。据报导,这个U签证已成为法律漏洞,无辜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反成为“受害者”。蕾妮。孙(Renee Sun)女士的21岁儿子,就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一年前,一名来自蒙古的女学者,主动接近他并要求约会,和他一起上瑜伽班,了解他的信仰。交往期间,这位女朋友经常上演分手泪崩剧,每次都要求他“发短信”。孙女士的儿子和家人直到他被莫名逮捕后,才明白中了这个女朋友所设的陷阱,因为她向警方报案称孙女士的儿子跟踪她,证据之一就是他过去发的短信。孙女士说:“这是典型的设圈套诈骗美国年轻人的案子,这名女子的目的是为了她还有她的整个家人,获得合法居留美国的身份。找到像我儿子这样的受害者,他们可以因此留在美国,并立即享受所有的社会福利。”移民专家和孙女士相信,这名女子利用U签证的规定,制造她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孙女士的儿子是加害者的事证。多数妇女和儿童,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不了解法律和担心被驱逐等原因,遭到私贩人口、家
-
转眼,来到澳洲已经十多年了。其实当初并没有抱着移民的目的而来,但不知不觉却已经把澳洲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发现自己对澳洲的感情从最初的新鲜懵懂,到现在的习以为常,与身边不少同样来自中国的移民朋友的经历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今天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些年来的移民经历,希望为那些同样奋斗在澳洲的中国朋友们带来一些过来人的经验体会。初来乍到,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和很多人一样,我早早地离开了父母,来到澳洲求学。之所以选择澳洲,是因为这里美丽的海滩,宜人的天气,以及悠闲的生活态度。然而,刚开学就让我经历了不小的挫折。原来在国内学习成绩不错的我,太习惯与国内被动学习的方式,对澳洲以鼓励学生主动探究学习的教学方式居然有些无所适从,除此之外,我还需要克服语言的困难,与澳洲同学一起小组讨论、在全班同学面前做项目演讲。好在周围有不少和我一样的中国同学,我们相互鼓励和帮助,终于在半年后渐渐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也就是在第二学期,在一次同学组织的万圣节派对上,我认识了他。和我一样,他也是初来乍到的留学生,相似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有着聊不完的话题。派对结束后,我们互留了电话,后来的我
-
写在前面的话:很多人知道我是个写励志故事的姑娘,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已经在房车上住下八个多月。在新西兰这个国家,能够以这种方式生活,乃我人生首要大幸事。我在夏天驾车走走停停,冬天则把车停在房东家的院子里,努力工作为了下一个夏天赚旅费,日子充满惊喜与期待。下面是买房车最初写下的一篇文章,文末加上了新的照片和视频,希望你喜欢,也希望有一日之内,我能在这里请你喝一杯咖啡,坐在海边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与梦想。一个住在房车上的姑娘文/杨熹文 我向我的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的微信还是炸开了。 “你疯了吗?”“为什么不去买个房子呢?”“该不会……是最近手头紧吧?需不需要我帮忙?” 别紧张,我没有失恋没有破产没有流离失所,只不过我这个89年的老姑娘,扛着所有身家,搬进了一辆89年的老房车,铺了床,生了火,在冰箱里放上一排鱼罐头和冰啤酒,真正开始了我晃荡十足的后青春生活。我的房车七米长,是那种很久前在日本被淘汰掉的20人座小巴士,飘扬过海到了新西兰,曾经被不同的人开去不同的地方去做不同的事,易主几次,饱经沧桑,收关停在了一对八十几岁老夫妇的门前。这对八十几岁的前车主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这部
-
(一)我和一个在奥克兰的姑娘聊天,她正在走着我走过的那条路。她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几年前拿Working Holiday签证来新西兰,打工攒了一年的钱,然后申请学生签证去读书。这是读书的收关一年,也是她最苦的一年,整日在学校和打工地方之间穿梭,也时常焦虑着用什么方式可以留下来。姑娘读两个major,住在地区偏远房租便宜的合租房里,生活中“基本上干什么事情都要算一下经济成本”,只此值钱的资产是一部车,为了省房租恨不得搬到车里住。她的性格坚强又乐观,尽管说着“每天不是去上课,就是在打工,都不舍得回国。因为房租要交着,还得买机票。”却还不忘告诉我如果到了奥克兰她一定要带我去吃正宗的凉皮。能在二十几岁时以老十岁的架势去拼命的姑娘,都是有苦衷的。我看到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在这里自己多赚一纽币,父母就能少赚五块钱。”我的心跳静止,眼泪却狂飙。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有多少面露忧愁的黄皮肤,置身于不属于自己的热闹里,影子一般地走过来又走过去,拼命在找一处可以落脚的安全区。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怀揣着一张800人民币的签证,低着头,拼了命,在走一条无法确定忧喜的移民路。(二)微博里出现过一篇《再见北京》的文章
-
聊天片刻今天陶朗加下雨,我的心情却很棒,早上和朋友Glenn见面,陪他练习中文对话,然后一直聊天到下午一点半。我在图书馆里坐足了三个小时,做完了待办事项的绝大部分,想起朋友对我开的玩笑,“天哪,每天写写写,如果把你的大脑打开,那里面肯定肌肉丛生!”也许是吧。窗外依旧飘着雨,这几天可以看到超级月亮,听说新西兰的地震和它有关,为受难中的人祈福。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依旧在这里,絮絮叨叨和你讲我生活中的那些事。双十一结束了,希望你的银行卡永远有为自己买一本书的余额。我和小千说,“等咱店里推荐到首要万本书的时候,就开个咱们自己的书店吧!”为这个梦想,努力。有一个姑娘给我留言,言语间充满绝望,“当我看着同龄的姑娘嫁给有钱人家,过上了我靠自己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过得上的生活,没有谋生存的压力,只有逛街spa做美容,去哪里都车接车送,回家保姆伺候……我问自己,读这么多的书,考那么多的证,在社会上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这些还有什么用?”我答应一定要写篇文章给她,这不是一个人的绝望,是一个群体的心声。随便在哪个拥挤不堪的公交车站望去,你总会望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姑娘,她们穿着高跟鞋和西装裙,极力
-
热线4009 933 922
-
客服
-
小程序

无需下载看项目
-
公众号

海那边公众号
-
微信群

加入海外移民交流群
-
APP

微信扫一扫,下载APP
-
返回顶部
����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