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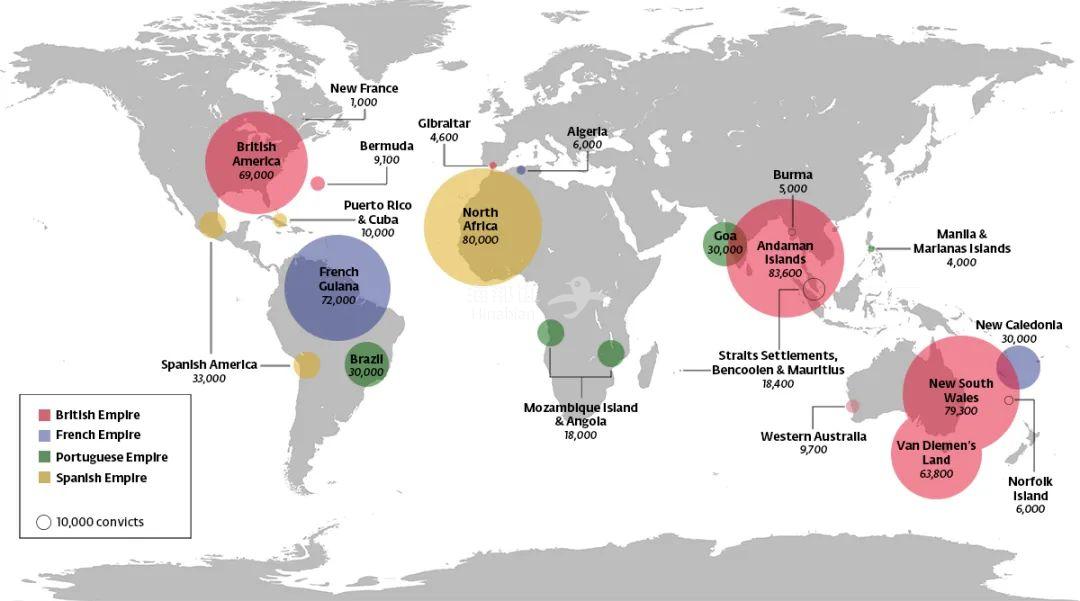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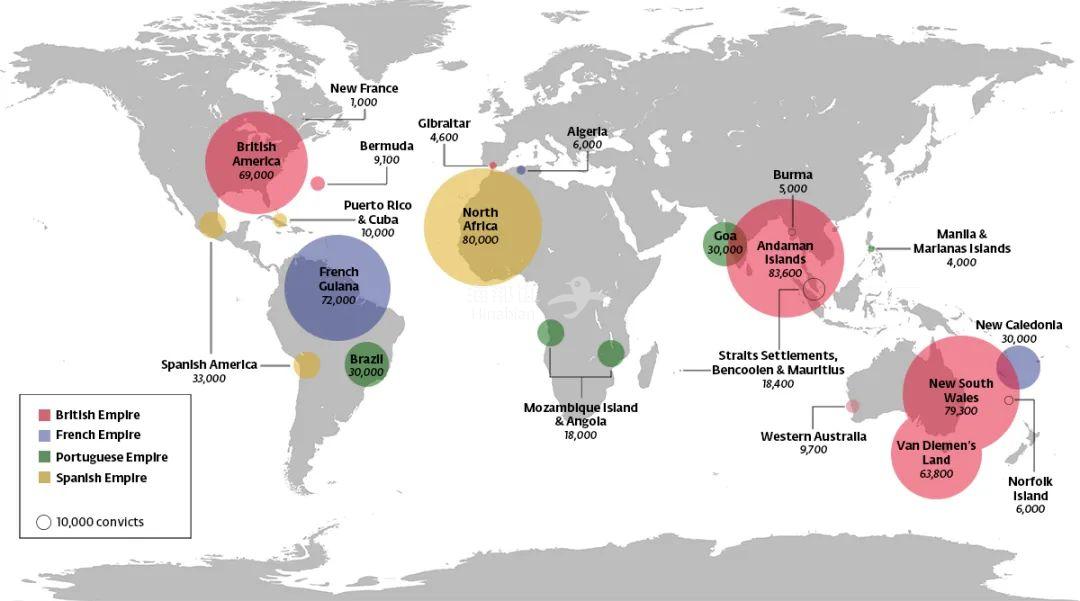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移民工具箱

海那边公众号
新时代移民内参,为您开启 海外优质生活
 微信 扫一扫
微信 扫一扫

海那边移民
无需下载看项目,专家答疑
 微信 扫一扫
微信 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