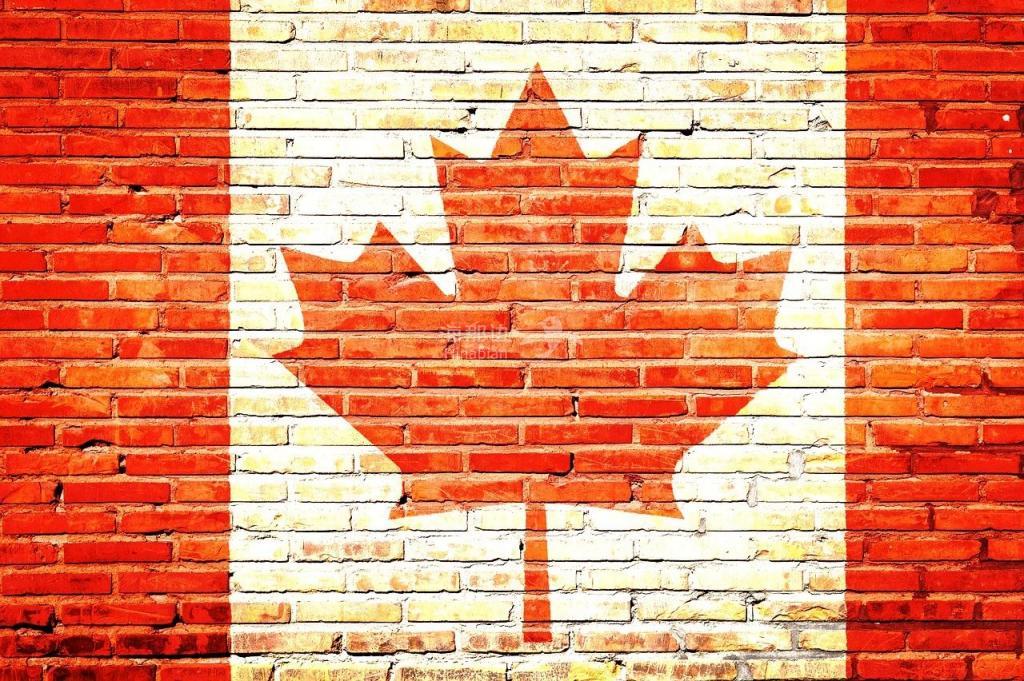BC省2018市选实际上在同一时间进行着两场竞争。一场是争取政府席位掌握城市发展方向,竞选焦点集中在选民关心的民生议题。比如温哥华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可负担性住房,支持小企业的发展”,素里的“降低犯罪率和天车计划”。选举政纲基调是向前看,给人描绘出执政后城市的前景。
另外一场发生在华人内部,不太接地气,纠结在谁能代表华人利益。主要基调是“秋后算账”。谁反对过大麻合法化?谁支持过同性恋教育?人家忙着抢西瓜,我们忙着拣芝麻。结果是那边选举大局已定,这边还意犹未尽。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按道理,政府选举是民主生活的“嘉年华”。选民平时人微言轻,选举时才扬眉吐气,应该高兴才对。可是华人圈子出现了选举焦虑症,“急吼吼”地带着暴戾之气。人为制造紧张空气,好像华人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不发出“收关的吼声”就完了。
有人将候选人非黑即白地分类。“自己的人”真正代表人民,是“良心候选人”。意思是其他候选人没良心或是黑心肠,都是祸国殃民之徒?有人把选举变成了扬善除恶的战场。甚至有人高呼“变天”。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
有人把民主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其实,人民只是一个并不实际存在的政治概念。你是人民一员,我是人民一员,但你不是人民我也不是人民,那么谁来做主?过去是帝王做人民的主子。而1620年“五月花公约” 开创了人民推举某些人为民做主,或者说做民之主的先例。
五月花号是一条从英国开往北美洲弗吉尼亚殖民区的客船。船上有殖民者、清教徒和契约佣工等共102名移民。由于气候恶劣航线偏离,他们到达了一个陌生的荒凉之地。此时此地,他们“无法无天”,没有合同,法律或政府约束。但他们没有选择“自由”,而是签订了对自己有约束力的“五月花公约”。为什么?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情投意合。实际上,五月花号在航行中和登陆前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纠纷。正是如此才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自相残杀或者各自为政,他们很难在严寒荒凉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
在公约形成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维权”意识不断弱化,从相互包容中升华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共识。公约以“人民自治”否定了王权与神权的统治。同时,也以“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形成自我管理的社会制度。
“五月花公约”的诞生说明维权只是本能,宽容少数和服从大多数才是高层次的民主。比如,政府在你的社区为流浪汉建组合屋,可能带来安全和卫生问题,所以你有理由反对在你家“后院”建组合屋,这属于维权层次。
如果你反对到处建组合屋,理由是这样扰民伤财,还解决不了流浪汉问题,这就提升到了“议政”层次。如果你提出自己的方案,不扰民建组合屋也能更有效地解决流浪汉问题,这就是到了更高的“参政”层次。
这三个层次都是民主,但档次不同。显然,如果华人只在“维权”层次上打转转,把争取“华人利益”放在首位,在选举中必然很难出头。所以,华人参政要接地气,不要把竞选市民的当家人,当成竞选华社首领。华裔候选人应该把精力放在大多数选民关注的议题上,提出建设性可行的政见,才能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点击图片,加入移民交流群)